一、史铁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国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市。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命。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苦恼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韩少功评?史铁生完成了许多身体正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对于人的命运和现实生活的冲突,没有停留在表面进行思考,而是去拷问存在的意义。——邓晓芒评史铁生绝对是新时期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不是通过作品传达思想,而是引导读者自己探索生命的意义——王又平评史铁生当然是杰出的。因为他是个残疾人,所以他的作品中有别的作家所没有的一股静气。史铁生的作品过于关注生死、宗教、信仰等问题,有人对这一点持保留意见,但我觉得他的思想是有深度的。——王蒙评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莫言评扩展资料谈到史铁生,相信大家都会想到《我与地坛》中那个身残志坚的他。在一次文学访谈中,史铁生,这个生于中国北京的散文家、作家,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文学态度:“面对灵魂的写作。”也许是自古老天妒英才,才会制造出各种困境来为难这些才华横溢的天才。而能走出困境成材者,一定拥有着常人无法感同身受的艰苦经历,以及常人无法企及的吃苦的精神。我们作为他人生活的读者与观众,太容易只被其表面风光吸引,而忽视风光背后的泪水。就像我们读史铁生的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豁达感一样,殊不知这字字句句的背后都浸透着这位作家对世界、对命运的探寻与质问。 2010年12月31日,在与病魔斗争了30多年后,史铁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这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他没有挺过去,本来再过4天,就是他60岁寿辰。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所以他60岁“生日”那天,张海迪身穿红色大衣而来,献上60朵红玫瑰;铁凝提着一篮子樱桃而来,因为史铁生曾在他面前说过“樱桃我爱吃”。北京798时代空间画廊,几百人给史铁生过“生日”,现场没有花圈和白纱,没有牧师和挽联,只有鲜花和红装,只有怀念和祝福,60根红烛绕成一圈,一张张祝福卡片写着“铁生,生日愉快”,“铁生,一路走好”。我想,最有尊严的死亡,莫过于此了吧。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铁生
二、史铁生的简介
史铁生简介 史铁生(1951—),北京人。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2年、1983年全国杰出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后,于1969年插队延安,1972年因病致瘫,转回北京,1971年到1981年在 北京某街道工厂做工,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1979年开始创作,1983年和1984年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荣获全国杰出短篇小说奖。 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五万元)。小说记述他在初残后工作于街道小厂时的经历。有人称誉它:“怀旧但不感伤,冲淡悠远,充满寓意。”另外,余华的短篇小说《我的故事》与陈军的中篇小说《禹风》、苏童的短篇小说《棚车》(各三万元)获二等银奖。《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获得《作家报》1996年十佳小说奖。1997年当选北京作协副主席。 下面这个是他自己的辩论 一 人为什么要写作? 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扰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 区分人与动物的界线有很多条,但因其繁复看似越来越不甚鲜明了,譬如“思维和语言”,有些科学家说“人类可能不是唯一能思维和说话的动物”,另一些科学家则坚持认为那是人类所独有的。若以我这非学者的通俗眼光看,倒是有三条非常明显又简便的区分线摆在这儿:会不会自杀(是会不会,不是有没有)。这天地间会自杀的只有人类。除了活着还要问其理由的只有人类。丰衣足食且身体健康忽一日发现没有了这样继续下去的理由从而想出跳楼卧轨吃大量安眠药等等千条妙计的只有人类。最后,会写作的只有人类。 鲸的集体上岸“自杀”呢?我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我猜这准是相当于醉后的坠入茅坑之类,真正的自杀是明确地找死,我看鲸不是。倘若有一天科学家们证明鲸是真正的自杀,那么我建议赶紧下海去买它们的书,我认为会自杀的类都是会写作的类。 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愉快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虽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易,简易到容易被忘记。 二 历史上自杀了的大作家很多,是怎么回事?是自杀意识导致写作行为呢还是相反? 先说后面一个问题。至少文化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在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固然仍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但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自杀的事情就更多。 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 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恳!——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恳,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好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静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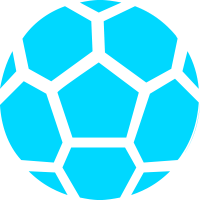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产品展示
产品展示
 热门广告
热门广告
